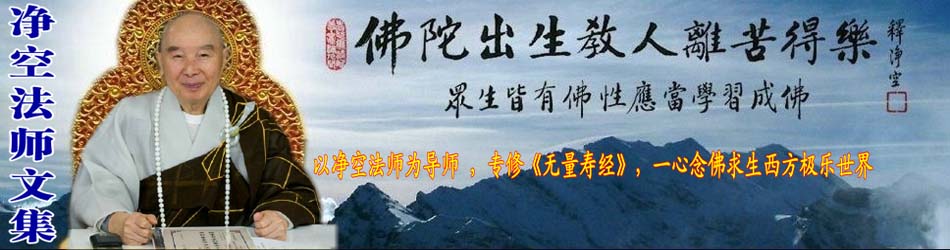淨土聖賢錄易解卷5-2
明 袾宏(蓮宗八祖)
袾宏。字佛慧,號蓮池,杭州仁和沈氏的子弟。年十七歲,中秀才,以學問德行著稱。鄰居有一位老婦人,每日念佛號數千,袾宏問她是何緣故,老婦人說:「我的先生持佛名號,臨命終毫無病苦,與人拱手作別而往生,因此知道念佛的功德,不可思議。」袾宏從此之後即歸心於西方淨土,書寫『生死事大』四個字,放在桌子前面,以自我警策。年三十二歲出家,拜謁融、笑巖諸長老大德,參究『念佛的是誰』,有所省悟。
明穆宗隆慶五年(西元一五七一年),乞食到雲棲山,看到山水景色極為幽靜,於是定居下來。雲棲山本來一向多虎,袾宏為之放瑜伽燄口,虎即不再為患傷人。有一年大旱不雨,居民請求他為大家祈雨,蓮池大師回答說:「我只知道念佛,並沒有其他的方法。」大眾堅持地請求,大師於是就拿木魚出去,循著田埂而行,稱念佛號,即時大雨如傾盆般地跟著下起,隨著大師腳步所到的地方即下起雨來。眾人非常歡欣喜悅,於是互相聚起來為他準備建材、造立屋舍。四方的僧人也日漸地前來親近歸附,於是此處成為一叢林。蓮池大師主張淨土法門,痛斥狂禪。著作《阿彌陀經疏鈔》,融會事理,統攝上中下三種根器的眾生,內容極為淵博深奧。當時有一位名為曹魯川的居士,寫信給蓮池大師,其中大略是這樣的:
「夫釋迦牟尼世尊有三藏十二部的教典,這就是所謂在廣闊的大海,張開眾多的網,又所謂有大的倉庫也有小的倉庫。我們只應該談大以包容小,怎麼可以反過來舉一而廢多呢?最近我們鄉里間有在倡說要經無量劫才可以成佛,只有漸次修行而沒有頓悟成佛之事。這種『歷劫成聖,必漸無頓』之說的漸教,雖然也是聖人說的,未嘗有不是之處。但是以漸教而廢棄頓教之法,那就有差錯了!尊者(指蓮池大師)您內心秘密地體悟圓頓的教法,而外在顯示淨土法門,諸佛也是有這樣在度化眾生,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。奈何最近以來這些聽教的信眾,只想要以阿彌陀佛一位聖人,而盡廢其餘的十五位王子(註:《法華經》(化城喻品)中,大通智勝佛有十六王子,皆已成佛,阿彌陀佛是其中之一。)。以淨土一部經典,而廢除三藏十二部的所有經典。那麼這是不才如我者所不願聽聞的。
當今雖然是末法之時,然而眾人的根機,難道沒有利根、鈍根的差別嗎?有如釋迦世尊,為大迦葉、為憍陳如,他的說法是如此。為善財、為龍女,他的說法又是另外一種。《楞嚴經》中,二十五位聖人,各個證得圓通,而文殊菩薩所稱歎的,又是不一樣。正是所謂的昨日定,今日不定。又所謂說:我是空,而且又不是空;說:我是有,而且又不是有。這就是能夠善巧方便應機說法,而不專執一門為主。活活潑潑地,如水上葫蘆一樣,按了就轉動,限制不住它。假如像木樁釘住一點、守住一個洞窟,怎麼能夠利益人天大眾呢?我所期望的,希望尊者您,為凡夫大眾開示淨土法門,而遇到利根器的就直指最上乘的佛法,能夠圓融通達,不限制於一個立場角度。使得大鵬鳥和小麻雀,各自安適於自己的處所,這樣不是盡善盡美嗎?
另外,佛陀所說的《華嚴經》,乃是無上的一乘圓頓教法,是如來稱乎本性的究竟了義之說。尊者您卻以之與《阿彌陀經》並稱,這樣好像已經有些不妥當。您又因此而著作論疏(指《阿彌陀經疏鈔》)讚歎高推極樂淨土,使淨土法門凌駕於華嚴之上,所謂的『朱紫混淆』大概就是說這種情形吧!因此我同時期望尊者您,為淨土根器的人說淨土法門,為華嚴根器的人說華嚴,大家不要互相譏誚攻擊,但是也不要相互混雜紛亂,這才是真正的流通佛法,才是五教同時宣揚,三根全部攝受,何必一定要刻舟而求劍(指因無知而用錯誤的方法,去追求想達到的目標。),彈雀而走鷂(指因小失大)呢?」
蓮池大師回信曰:「華嚴具足了無量的法門。而求生淨土,也是華嚴無量法門中的一門。就時代的機緣而言,我們的本意是要藉由此淨土法門而入於華嚴的境界,並非是要推舉此一法門而廢除華嚴。你來信說我以《阿彌陀經》與《華嚴經》並稱,因此而有著作論疏,使淨土法門凌駕於華嚴之上,如果真有這樣的論著,此論著又是誰作的呢?要知道,華嚴就如同天子,有誰能使王侯大臣種種百官,凌駕於天子之上呢?就算是我也不曾使之平等並稱啊!我在《阿彌陀經疏鈔》中,特別說明了華嚴是究竟圓滿的道理,而《阿彌陀經》只得到此究竟圓滿的少分,是華嚴經的眷屬之類的,因此兩者不是並稱的。
其次,來信又說,應當隨著眾生的根機給予教化,為適合淨土的人說淨土,為適合華嚴的人說華嚴,此意甚妙。但是其中有兩個意義:第一、『千機並育』,千種根機的人都能夠得到教化,這乃是如來出現於世間的大事,並非敝人我所能作為的。因此曹溪六祖專弘直指人心的禪法,豈是六祖不能通達其他的教法?慧遠大師建立東林的蓮社,也不是只會接引鈍根的人。至於雲門、法眼、曹洞、溈仰、臨濟,雖然五宗同出於曹溪六祖之根原,然而其教授指導眾生的方式也稍有差別。各個門派祖師,施設不同的方便教法,本來就是這個樣子,沒有什麼好奇怪的,何況是像我這樣一個凡夫呢?如果隨便地學習古人,昨日定,今日又不定,散漫而沒有一定的師承,多變紛亂而不專一。名義上說是要利益眾生,實在是誤人子弟。何以故?『我為法王,於法自在。』只有法王才可觀察眾生根機給予不同的教化。我們自知是平民,卻要號稱國王,這就不可不謹慎小心了!
第二、演說華嚴則必然收攝淨土,說淨土也一樣可以貫通華嚴。因此說華嚴的自己專說華嚴就好,說淨土的就自己專說淨土,這固然也是可以並行而不違背的。然而現今之人只知道華嚴比極樂淨土廣大,卻不知道阿彌陀佛即是毘盧遮那如來。另外,龍樹菩薩入出龍宮誦出《華嚴經》,而卻願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普賢菩薩為華嚴會上的法王長子,卻又願生西方極樂。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一同輔佐毘盧遮那佛,號稱華嚴三聖,也同樣願生西方淨土。這些都有確切的依據,就如同明月星辰一樣的明白清楚。居士你將提倡華嚴使之風行四方,而卻與文殊、普賢、龍樹等菩薩的願力相違背,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。
況且李通玄長者所著的《西方合論》裡列出十種淨土,極樂雖然說是權宜,而華嚴權實融通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因此淫房和殺生之地無非是清淨的道場,何況七寶莊嚴的極樂世界呢?婆須密多以淫欲度眾生,尚且皆是古佛示現的妙用,何況萬德莊嚴悲智具足的阿彌陀佛呢?居士你遊戲於華嚴的無礙法門之中,而卻礙於極樂淨土,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。我和居士你同為華藏世界的莫逆之交、同道良友,而居士你卻不明白我區區之心。而且我又願意拉居士為極樂世界清淨蓮胎的骨肉兄弟,希望居士你不要置我於外啊!」
曹魯川居士又寫信來說:「諸多不是究竟了義的經論,例如普賢行願品和《大乘起信論》,都稱讚演說淨土法門,這豈是沒有原因的?然而在《華嚴經》中,卻未曾提及。這在《西方合論》中所列的第十淨土就更清晰明白。《法華經》裡所列出的十六王子,裡面雖有阿彌陀佛,但是並未曾定為唯一的至尊。其中讚歎持經的功德,旁枝地說到極樂淨土,實在是在說明女人往生淨土的因果。《首楞嚴經》中二十五位聖者所證的圓通,文殊菩薩並沒對其分別高下,只說『方便有多門』,又說『順逆皆方便』。但是以修行的快慢不同,在沒有高下差別之中,又未嘗沒有指示和歸向的目標。因此歸結於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為最上,而不推崇讚許大勢至菩薩為第一。又更加貶斥評論為:『無常』,為『生滅』。
而像賢首、清涼等大師,極力地標示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等五教,這是大家都認為得體適當的,可是其中卻未嘗評論到淨土。禪宗這個門派,尤其是特別地掃蕩排除淨土法門。例如齊己禪師說:『唯有徑路修行,依舊打之繞。但念阿彌陀佛,念得不濟事。』又說:『如果和以前一樣地捨父逃走,流落他鄉,東撞西磕,苦哉阿彌陀佛!』像這一類的語言,有人以為是太苛刻,可是難道是毫無原因的嗎?而齊己禪師既然這麼說,想必是有他的道理啊!
所以通達佛法的人一再地說道:『無量阿僧祇劫的辛苦修行,不如於一念間證得無生法忍。』又說:『於當下一念緣起悟入無生,就能超出三乘權巧方便之學。』何況無論三乘或一乘,主要就是在說明『無我、無我所』,而今天往生淨土的人,念佛的我為能生,極樂淨土為所生,自他能所的分別極為清楚,生滅的現象極為明顯,而愛憎取捨的心念又紛亂不止,這些種種的缺失,真是多得無法盡舉。我們看看自古以來弘揚淨土法門的人,必定說:『華開見佛悟無生』,一定要往生淨土見了阿彌陀佛,才能從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,或者阿彌陀佛,教誨他一切法無生的道理,這個時候才能開悟,如此似乎是比較曲折遲緩。
再說華嚴世界毘盧性海所現的法界全身,就如同人身有八萬四千毛孔,而東方的藥師佛、西方的阿彌陀佛,各各在其中的一個毛孔,說法度眾生。假如我們拋棄掌握全身的機會,而入於一個小毛孔,這不但是把大海與水泡本末倒置,又像是蒼蠅不投向廣大的虛空,而猛穿窗紙以求出路,這些比喻大概就是在說這種事吧!先前不才我所寫的書信中所說的:『為適合淨土的人說淨土,為適合華嚴的人說華嚴。』我自認為是不違背諸佛的法門,也是為了尊者您本人的片片真心。而尊者您卻想要牽引我入蓮池苞胎,那就如同古人所說的:『把人捉入迷途中』,以及所謂的拋棄金子而擔取稻草一樣。
尊者您座下的聽者徒眾,從杭州來到蘇州的人,無非津津樂道於九品往生。私下地和他談論,只要一涉及上乘佛法,則駭然心驚、張大眼睛發楞而不知所措,有的更反過來嘲笑上乘佛法,像這種過失,是在弟子們呢?還是在大師您呢?大丈夫的氣勢胸量,應當浩然沖天,以廣度眾生為急務。既然已經捨俗出世了,也開堂授徒了,也敷座弘法了,不但不具有大丈夫的作為氣度,反而只有街坊老齋公、老齋婆的行為舉止,等到突然被伶俐的人問著,被明眼人逼到,不知道是要向虛空北斗中藏身,還是要向鐵圍山裡藏身呢?佛法大事非同小可,希望尊者您重新審慎思量吧!」
蓮池大師又以書信答覆說:『委屈您賜來的書信之中,玄妙的言詞、高超的辯才,深沈廣博層層無窮,實在是令人欣羨之仰慕之。然而我私自以您關愛我至深,而言詞卻太過浪費周章了,如果您想要弘揚禪宗、貶抑淨土,也不必說很多,何不說:『三世諸佛,被我一口吞盡。』既然一佛也不立,哪一個更是阿彌陀!又何不說:『若人識得心,大地無寸土。』既然寸土都沒有了,何處更有極樂世界!只要用這兩句話,那麼你來信的內容就攝無不盡了。如果我現在要一一回答你,恐怕犯了鬥亂諍論的過失;如果不回答,則此於佛法深義大有關係,終究不可以沈默不語,所以膽敢在此約略地陳述之。
你書信說到不了義經典才談說淨土,而以(普賢行願品)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當作談淨土的不了義經。《大乘起信論》暫且不說,(普賢行願品)以一品而統攝八十卷《華嚴經》之全部經義。從古至今,誰敢議論其為不了義經典。居士您獨推崇《華嚴經》,而卻排斥(行願品),(行願品)是不了義,那麼《華嚴經》也是不了義了!另外,你來信又說《法華經》授記往生極樂淨土的,是女人修持的因果;那麼,龍女成佛,也只是女人的因果嗎?你又說阿彌陀佛只是十六王子之一;那麼毘盧遮那佛也只是二十重華藏世界的第十三層而已啊!居士您獨尊毘盧遮那,奈何您卻不知毘盧遮那與阿彌陀是平等不二的。
來信又說到《楞嚴經》選取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,而捨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,更貶斥之為無常、生滅。那麼憍陳如尊者體悟『客塵』兩個字,可以說是通達無常而不取無常,並以此契入不生不滅的深義,何以不能入選為圓通法門呢?果真說:『觀音登科中舉,勢至下第落選。』難道你不曾聽說『龍門點額』之比喻(龍門點額是古代傳說,鯉躍龍門,若越過者魚化為龍,若不過者則只是龍門點額,依舊為魚,用以比喻雖是科舉落第的人,未必無有真才實學。),而卻作齊東野人之道聽塗說!
你的來信又說到齊己禪師,將古人勸人念佛的偈頌,逐句的註解其語,古人說:『唯有徑路修行』,則附註說:『依舊打之繞』(依然輪迴打轉)。古人說『但念阿彌陀佛』,則附註說『念得不濟事』(念了也無濟於事)。居士您既然通達禪宗之法,為何不知道這是禪宗祖師當下為人解除執著、捨棄束縛的方便語,如今你卻把它當作真實不變的教法去體會,而死在語言文句之下呢?若是如此,古人有言:『踏在毘盧頂上行』,如此則不但阿彌陀佛無濟於事,毘盧遮那佛也無濟於事。像這樣子的語言,祖師大德的語錄傳記之中,有百千萬億之多。老朽我四十年前,也曾用這些話來逞口舌之快,用之來自豪自己的文章。後來知道慚愧了,從此再也不敢如此去做,到了現在回想起來,仍然感覺到羞愧臉紅耳根發熱呢!又齊己禪師說:『求生西方的人,猶如捨父逃走,流落他鄉,東撞西磕,苦哉阿彌陀佛!」現在我可以回應他說:「如今卻是如子憶母,還歸本鄉,捨東得西,樂哉阿彌陀佛!』居士您且說說看,這句話和齊己禪師所說的相差多少?
又來信說道:『多劫修行,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。』居士已經證得無生法忍了嗎?如果已得,則不應該以念佛的『我』為能生,以『淨土』為所生。何以故,即念佛心即是淨土,誰為能生?即淨土即是自心,誰為所生?不見能生、所生而往生淨土,故終日生而未曾生,這才是所謂真正的無生。如果一定要人不可以往生,然後才稱之為無生,這是斷滅空,不是真正『無生』的旨意啊!來信又認為以『華開見佛,才能夠體悟無生。』則是曲折遲緩。居士您通達禪宗,難道不知從執迷而得開悟,就如同從睡夢中醒過來,又如同蓮華開放。念佛的人,有現生見性的,是蓮華頓時盛開的。有往生後開悟見性的,是蓮華開於比較久遠之後。眾生的根機有利鈍之別,功行也有勤奮與懶惰之分,因此華開有慢有快,怎麼可以一概以為曲折緩慢呢?
又來信把華嚴比喻為人的全身,把西方淨土比喻為毛孔。往生西方的人如同把全身放入毛孔之中,是大海與水泡本末倒置,像這樣子的大小比喻是沒有錯的。但是,居士您既然通達華嚴宗的思想,怎麼只許以小入大,不許由大入小。況且大小相入,正是華嚴十玄門的一玄啊!舉華藏境界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盡的世界,而入於極樂淨土的一朵蓮華中,尚且不能盈滿此蓮華一片葉子中一芥子那麼微小的地方,那麼又何妨把全身投入於一毛孔之中呢?
來信又告訴我這個荒山野僧說,只要問到上乘佛法,就駭然心驚張大眼睛發呆。居士您不是說:『適合華嚴的要告訴他華嚴,適合淨土的開示他淨土法門。』如今這些鈍根之輩,正適合求生淨土,你何不給他適應病症的藥,而強要喧擾吵雜他們呢?你又說道,老朽我既然出世修行開堂授徒,不具有大丈夫的作風謀略,而作老齋公老齋婆的行為舉止,一旦被伶俐人問到,被明眼人逼迫到,是要向虛空北斗裡藏身呢?還是要向鐵圍山裡藏身呢?
老朽我從來不敢承擔『出世』之名,自己認為也沒有什麼『大丈夫』的作風謀略,這些姑且放下不談。而居士您把修行淨土的人,貶斥輕視為老齋公老齋婆,那麼就如同古人所說,這不是貶斥愚夫愚婦,而是貶斥文殊、普賢、馬鳴、龍樹等大菩薩啊!豈只是文殊、普賢、馬鳴、龍樹,還有慧遠大師、善導大師、天台智者大師,永明延壽大師等諸菩薩、諸善知識,都是齋公齋婆嗎?劉遺民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蘇東坡等諸大君子,都是齋公齋婆嗎?就算是齋公齋婆好了,只要是念佛往生者,即得不退轉菩薩之地位,怎麼能夠輕視貶斥呢?況且齋公齋婆,雖然平庸無智低下卑劣,然而卻是很恭敬地遵守戒律規矩,像這樣是正確的,還是愚痴呢?而那些聰明智慧善於言詞辯論的人,喜歡任意狂妄地談論般若,在吃肉吃飽了之後,又來找僧人閒聊禪理的人,真是魔啊!愚人的長處就在於他能安於樸實木訥,我自己曾真心地思惟:我寧願被說是老齋公老齋婆,也不願做老魔民老魔女!
至於所謂的伶俐人、明眼人來問到、逼到,那麼老齋公老齋婆不須高登虛空北斗,也不必遠赴鐵圍山,就只要在伶俐漢的咽喉處安單居住,在明眼人的眼珠裡敷座而坐,何以故?要教他暫時閉住口頭三昧,要他回光返照。居士您推尚華嚴而極力的毀謗淨土,老朽我專修淨土而不斷地讚歎華嚴,如果居士你靜下來的時候,暫且試著去思惟一下,此事為什麼會這樣呢?
又你來信說我勸你求生淨土,就譬如叫你拋棄金子而擔取麻草,是顛倒行事,太過於屈辱居士您了!但是我以為這樣的比喻尚未親切,現在代為作一譬喻:
譬如有一農人,拜訪於大富長者的豪門之前,拿出請帖,想要邀請大富長者到他的田園農舍。旁邊聽到的人都嘲笑他,可是農人卻又重新再次打掃自己門前的小路,準備再去邀請富人前來遊玩。在旁嘲笑這位農夫的人說:『富貴的主人前一次沒有責備你,已經是很幸運了,難道你還要再去邀請一次嗎?』農人回答說:『我看到很多富貴的人家,有的是雖然富有卻沒有仁義;有的是外表富有而實際上是貧窮的;有的是還未富裕就先驕慢了;有的是為富人掌管庫藏財物,而卻自以為是富人。況且像『金谷』這樣美的花園、像『郿塢』這樣巨大的庫藏,於今又在哪裏呢?而我以一介田園農舍的老翁,安享自在太平之樂,因此忘了自己的低下卑賤令人憐憫,而卻去邀請大富長者與我同享田園太平之樂,我現在知道錯了!』於是大家相視大笑而散去。」
蓮池大師平日廣修一切善行,以資助淨土的行業。當時戒壇久已停止而不傳戒,蓮池大師於是令求戒的人,自己具備三衣,在佛前受戒,蓮池大師為之作證明。大師又訂定《水陸儀文》、以及《瑜伽燄口》等儀軌,以救拔幽冥眾生之痛苦。並開設放生池,著作《戒殺文》,因此而受度化的人甚多。
明神宗萬曆四十年(西元一六一二年)六月底,忽然進入城裡,告別弟子們和故舊朋友說:「我將往他處去。」回到山裡之後,設茶點告別大眾,大眾都莫測他的意思。到七月初一的晚上,入法堂說:「明日我就走了!」第二天晚上,入方丈室,示現些微的疾病,閉目靜坐。等到城裡所有的弟子們都來到山上,蓮池大師於是又張開眼睛說:「大眾老實念佛,不可搗亂作怪,莫壞了我的規矩!」然後面向西方稱念佛名而往生,時年八十一歲。(雲棲法彙)
明 如榮
如榮。字大賢,杭州(浙江)海寧縣人。壯年時從事屠宰業。有一天,為豬所咬傷,心中突然有所感觸體悟,於是到縣城之北的寺院,剃髮染衣為僧。後來歸投雲棲蓮池大師,當時已經六十歲了!白天隨著大眾操持作務,夜裡則持誦佛名,精進勤勞而不懈怠。明神宗萬曆九年(西元一五八一年)生日的那一天,設置齋飯供養大眾僧,長跪於佛像蓮座之前,高聲稱念『願生西方』者三次,大眾環繞著為他念佛,然後安詳地合掌而往生。(雲棲紀事)
明 如清
如清。字法原,俗姓阮,紹興(浙江)上虞縣人,剛開始出家於西湖的龍井寺,後來進入雲棲山依止蓮池大師,於是更加堅志念佛。除了念佛之外,又誦《法華經》,六時禮拜。明神宗萬曆十一年(西元一五八三年)得疾病,重病臥倒在床持續了數個月,有一天病危時,聽到大殿中的念佛聲,忽然張目注視地坐了起來。到了半夜,合掌恭敬地注視著阿彌陀佛的金容,頭部向上仰慕企盼而往生。(雲棲紀事)
明 廣製
廣製。字安廬,不清楚他的出身,年少時夢見進入『金盤庵』合掌站立在琉璃燈下,面向著西方三聖的聖像,庵內寂靜而無人影,心中非常澄淨清澈,夢醒之後覺得非常快樂。年紀稍大的時候,又夢見進入『安隱庵』,看見觀世音菩薩作思惟憶念眾生的相貌。自此以後發起了出世修行的志願。年二十歲時出家,參拜雲棲蓮池大師,聽大師開示說西方極樂淨土沒有生死輪迴的痛苦,於是歡喜踴躍地說:「我從今以後,知道了歸向棲息、安身立命的地方了!」於是專精研究淨土法門,作懷想淨土的詩,以及許多的詞曲歌賦,大多是清新溫婉朗然可誦,現在摘錄他《懷淨土賦》的序言:
「所謂清淨太平的國土者,即是西方極樂的珍奇世界啊!其中讓人涉水遊玩的是清淨的瑤池和美玉的水洲,使人登高步履的則有七寶的階梯和金黃的行道。極樂世界遊化來去的都是證悟法身的大菩薩,是諸上善人所徘徊往來的地方。極樂淨土其世界的繁華、宮殿的美好,超過了仙鄉的玄妙廣闊,遠勝於天宮的莊嚴壯麗啊!所以諸佛交讚於十方世界,盛名記載於一切經典,難道不就是因為其國土的美妙殊勝,其修行成佛之簡易快捷嗎?不論是它的名聲超越於其他所有的國土,不論是體性不同其他的世界(只要具足信願行,帶業伏惑亦可往生,此不同於他方淨土。),只要一離開娑婆輪迴的地方而往生西方,最後必然能夠達到無生的果地。
如果不是出離世間厭惡五欲、怖畏生死無常者,哪裡能夠欣向仰慕淨土而志願喜樂之呢?如果不是窮究玄奧的不可思議境界,深信佛法確定不移者,哪裏能夠遙遠地懷想西方而愛好渴求之呢?這也就是我為什麼神往思戀、念念繫著,不論日夜夢醒之間心中總是懷想著西方,而好像我已經到了極樂世界一樣的緣故了!我洗淨了一切的根塵染污,將思念的心託付於安樂淨土,由於實在不堪憶念思慕之苦,因此姑且書寫極樂的美景以寄託我的情懷,其歌賦曰:
真如本性寂靜遼闊,始終不變而隨緣感現,有流逸於穢濁而成為充滿泥沙的世界,有繫念於清淨而成為黃金珍寶的世界。極樂世界所莊嚴的種種境界,實在是阿彌陀佛大行大願而成就的。因著世自在如來的因緣而發起,託著法藏比丘而確定真實的正基。極樂世界的殊勝莊嚴,或者在甚深的經典中被讚歎,或者受歌詠於種種的淨土詩中,這些都可由聖者真心的如實語之中得到印證,千萬不要以凡夫無知的妄想執著而產生疑問。極樂世界是那麼地遙遠幽深、玄妙美好,見識不廣的人守著自己的邪見而不能深信,信根淺薄的人執著於自己的妄情而不能明了。就如同小鳥低飛於蓬茅野草之間,沒辦法想像大鵬御風飛行於長空的優遊高遠。
理體如果沒有事相就不能彰顯,果地如果沒有正因也沒有辦法顯現。我顧慮到將來恐怕如同迷失的羊群一般、哭泣於生死輪迴的叉路上,因此我堅守執持佛號回歸極樂故鄉的穩當易行之道。由於親見了種種往生淨土的靈驗事蹟而發願西歸,看破自己的生命無常而隨時準備向西而行。依循著先聖修行的軌跡,棲息於永恒不死無量壽的庭園,假使諸上善人是那麼容易就可以與之相聚,又何必因不信而停留於疑城,剎那間解脫無始劫來生死的束縛,優遊於諸法無生的高尚情懷。
身披著輕柔的衣服隨風飄拂,手持著振動的金錫鈴鈴作響,籠罩於寶樹茂密枝葉的清涼覆蔭,踩踏著清新美妙朵朵盛開的蓮花。望著美麗蔚藍的天空心情高昂想要飛翔而上,於高處回顧著虛空而迅速往返。登高於天際間飛行的樓閣,俯看著幽遠深邃下界的大地,以任人高飛的蔚藍晴空為寶蓋,用高聳青翠的樹林為屏障。牽引隨風飄揚的綠葉枝條,撫摸含著晶瑩露水萬紫千紅的花朵。
雖然尚未登堂入室親見佛陀,但已經先得到長生不死之壽命,心意既然已經契合於一切法無生的妙旨,於是可以如履平地的深入於極樂世界重重玄妙之境界。緩緩地優遊於通達十方的道路,而條條道路毫無滯礙無不通達,任憑心眼空曠開朗地周視四方,隨意自在地逍遙往來。踏在柔軟而輕勾衣裳的如蔭綠草,步履於覆蓋著腳掌的落花繽紛,看看鸚鵡們輕盈地舞蹈飛翔,聽聽迦陵頻伽動人悅耳的歌唱。涉著蓮池的八功德水而出浴,隨著自己的意願而高低流動,滌除身心種種塵垢的污濁,洗去五蓋煩惱的昏昧迷蒙。
追隨遠公大師的芳軌,步履於善導大師的玄蹤,這個殊勝莊嚴的聖境,就是阿彌陀佛所居住的地方。兩旁的行樹整齊夾道而為引路,美妙芬芳的蓮華盛開相連以為居處。林間高聳著富麗堂皇的殿宇,四方座落著玲瓏朱紫的樓閣,美麗的紅霞流映在亭園的窗櫺之間,明亮的金光透照於綺麗的門庭之內。鳥兒晝啼而夜息,花朵夕合而晨開,天樂繁繞於微風樹葉之際,經典演說於流水響動之間。庭園內充滿著藍田的美玉,流水間淺沈著赤水之明珠,舉起衣祴以盛著供佛的花,飛越虛空前往諸佛身旁去聽法,突然地從此消失而出現於彼,恍惚之間時有而時無,任意地於剎那之際神通變化,就如同十方三世萬億的佛陀一樣。
內心寂靜氣定神閒,身心與世界都捨棄忘懷,凡事沒有任何的掛礙煩惱,在所有的因緣中,寂靜的真心從不生起一切相的執著。長飲般若智海之波濤,如大鯨一般吸食百川。駕御著清風而行,衣角隨風地高飛飄揚。法鼓琅琅清脆地振動迴響,異香芬芳濃烈地四處飄散。由林間經行而出的是蓮池海眾,於空中散落繽紛寶花的是天外飛仙。聆聽水鳥之法音,唱和著石中迸出的流泉,同時宣說空有之理,疏通聖教第一義諦之篇章。深入即相離相的境界,妙用出入於有無之間。齊一空有的差異而達平等之旨,忘情真假之分別而悟得甚深妙道。既然所謂的中道也不存在,同時也泯除了一心三觀的圓修。談不二之法於毗離耶城,推崇維摩詰居士的沈默不言;合萬物於自己之一心,回歸於同體本然的佛性。」後來不清楚廣製法師的去向。(淨土雜詠並序)
明 真緣
真緣。字慧廣,俗姓姚,常州(江蘇)無錫縣人。年三十歲出家,周遍地參訪於諸方的長老大德,經過了十六年,終於修得念佛三昧。
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(西元一五九四年),居住於浙江明州的阿育王寺,親眼見到佛陀的舍利放光,光中現出本師釋迦牟尼佛,於是發願要燃身供佛,逐一地去請求眾僧,希望大家布施枯木柴火,當時每個人都布施給他一束木柴,堆積起來而成為一個高座。真緣於是取香油塗滿身體,結跏趺坐在木柴堆上,合掌恭敬稱念佛號。當火勢燒到身上時,身體馬上變成灰燼。此時大眾皆看到五色的光,從真緣法師的頂門放射而出,光中現出菩薩的金身,高二尺多,光明照耀於四方上下,久久之後才滅去。(獪園)
明 傳記
傳記。浙江寧波鄞縣人,個性喜好獨居,每日以課誦《法華經》為主要的功課,讀誦的總數達到九千七百多部,世人稱為『法華和尚』。明神宗萬曆十四年(西元一五八六年),官員虞淳熙舉辦法華三昧懺,傳記法師長期禁足修習三次,總共修行了九個寒暑,屢次獲得祥瑞的感應。後來居住於杭州的西溪道上,親自挑水背柴,做種種的佛事,有人說:「和尚您還在作這些有為的功德啊!」傳記法師大聲的喝斥說:「無為法的功德豈在有為法之外嗎!」
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(西元一六一三年)七月,辭別弟子們,稱念佛名三千聲,唱《妙法蓮華經》經題四次,面向西方,合掌而往生。第二天,頂門仍然有暖氣,異香滿室。(法華持驗)
明 德清
德清。字澄印,晚年自號『憨山老人』,浙江金陵蔡氏的子弟。母親夢見觀世音菩薩抱個童子送給她,然後懷孕。等到誕生之時,有白色的胞衣重複地包著。年十九歲出家,精進用功專心念佛,有一天晚上,夢見阿彌陀佛現身站立於虛空之中,正好就在日落之處,阿彌陀佛的面容及相好光明,清清楚楚了了分明,自此以後,阿彌陀佛的聖相燦爛耀眼,時時顯現在面前。不久之後至五臺山修習禪定,體悟明白了本有的自性。後來又刺血書寫《華嚴經》,每下一筆,同時念一聲佛號,久了之後,動靜一如佛號不斷。
明神宗萬曆十年(西元一五八二年),清簡地閒居於牢山(山東膠州灣),李太后命令人送金銀給他建造寺院,並賜寺院名為:『海印寺』。太后曾多次派遣宮中的使者前往修造許多塔寺,當時有些與這位使者有怨仇的權貴人士,唆使東廠的太監假扮道士前往擊鼓鳴冤,以侵占的名義上報於朝庭。這件事牽連到了憨山大師,因此被判處『私造寺院』之罪,命令還俗並從軍駐守雷州(廣西)。憨山大師隨著他所到之處,穿戴著儒士的衣帽為眾生說法,又發下弘揚經典的大願,造論註疏《楞伽》、《楞嚴》等經典。
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(西元一六一四年),奉皇帝的詔令,恢復僧人的資格,退役回來時經過廬山,結茅庵於五乳峰之下,效法慧遠大師,依照六時的次序,更加精進地修習淨土法門。當時有一名為海陽的參禪人,向憨山大師求受戒法,因而問到修習淨土法門的要旨,憨山大師說:
「釋迦牟尼佛所開示修行了脫生死的方法,雖然說是方便有多門,但是只有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,最為直捷簡要。這個法門,乃是佛陀無問而自說,三根普被,四眾全收,不只是權巧為下根人施設的方便法門而已。經典說:『若要清淨佛土,應當要清淨自己的心。』現在要修行淨土的功業,必定要以清淨自心為根本。要清淨自心,第一先要戒根清淨。身的殺、盜、淫三業,口的妄語、兩舌、綺語、惡口四業,意念的貪、瞋、癡三業,這十種惡業,乃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三途的苦因。而今持戒的要點,首先必須三業清淨,如此則心地自然清淨。
於此清淨心中,厭離娑婆世界的痛苦,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,建立念佛的正行。然而念佛必定要生死心切,先能斷除一切的外緣,單單提起一念,以一句『阿彌陀佛』為我們的命根,念念不忘失,心心不間斷。二六時中,行住坐臥,不論是拿起湯匙舉起筷子,身體的轉動迴旋俯仰上下,或者動靜閒忙之間,於一切的時刻,不愚癡不迷糊,除了阿彌陀佛之外沒有其他的所緣。如此地用心,久久之後自然純熟,乃至於睡夢之中亦不忘失,無論清醒與睡眠一樣都能念佛如此則念佛的工夫綿密不斷,打成一片,這就是念佛得力之時也。如果能夠念到一心不亂,臨命終時,極樂淨土的境界現前,自然而然不被生死所拘束,感得阿彌陀佛放光接引,此是必定往生的有效驗證。
然而一心念佛執持名號固然是正行,又必須以觀想作為資助,如此則更為堅實穩當。釋迦牟尼佛為韋提希夫人開示十六種妙觀,便能於一生之間所作皆辦了生脫死。現在你應當於十六種觀法中,隨意選取一種觀想,或者單單觀想阿彌陀佛以及觀音、勢至二大菩薩的妙相莊嚴。或者觀想極樂淨土清淨的境界,就如同《阿彌陀經》所說的蓮華、寶池等等,隨著各自的意願作一種觀想。如果能夠觀想得清楚明了,則二六時中,好像現在就在極樂淨土中一樣,那麼臨命終時,於一念頃頓時就往生西方。應當要這樣地去用心修行,並且精持戒律言行,永斷惡念煩惱,以此清淨的本心,觀想憶念阿彌陀佛而相繼不斷,往生淨土的真正因行,不外乎就是這些了!」
又有一位名叫淨心居士的人問到:『念佛的工夫不能夠相續成片,請法師開示。』
憨山大師說:「修行第一個要點,就是要『生死心切』,想要了脫生死的心不真切,如何能夠念佛相續而打成一片呢?況且眾生無量劫以來,念念妄想紛飛,情執的愛根堅固障蔽了我們的本性,即使今生出家修行,何曾在短暫的一念之間痛切為了解脫生死。日用平常之時念念隨順著情執之流,未嘗反省思惟。今天只以虛浮的信心,就想要斷除多劫以來的生死,這就如同所謂的以一杯水要救一車木柴的火一樣,那裡有這種道理呢?
如果真的是生死心切,念念如救頭髮燃燒之急,只恐怕一失去人身,百劫再也難得人身。而將此一聲佛號咬住不放,一定要敵過紛飛的妄想。於一切處,念佛的心念念現前,不被妄想執著所遮蔽障礙。如此痛下苦到懇切的工夫,久久之後必然純熟,自然相應,不求工夫打成一片,而自然成片了!此事全部要靠自己著力用功,如果只是將念佛做表面工夫,那麼你修到驢年,也沒有得力受用之處,現在必須要勇猛精進,千萬不要再拖延懷疑了!」
憨山大師在廬山住了幾年,後來又到六祖慧能大師的曹溪道場。明熹宗天啟三年(西元一六二三年)十月,示現些微的疾病,告訴人們說:「老僧世緣將盡矣!」然後沐浴、焚香,端身正坐而往生,當時有一陣光明照耀了整個天空,享年七十八歲。(夢遊集)
明 傳燈
傳燈。俗姓葉,浙江衢州人(即今衢縣)。年少時跟隨著進賢映庵禪師剃髮出家。隨即參謁百松法師,聽聞《法華經》時心中恍然有所領會。接著又問百松法師何謂楞嚴大定,百松法師瞪大眼睛四顧而視,傳燈隨即契入。百松後來以金雲紫袈裟傳授給他。
傳燈一生修習《法華》、《大悲》、《光明》、《彌陀》、《楞嚴》等懺法,不曾虛度一日。後來居住於幽溪的高明寺。在此之前有一位當地人,名為葉祺,把親人埋葬於高明寺的後面。有一天葉祺夢到神人告訴他說:「高明寺這個聖地道場,將會有肉身菩薩在這裡大作佛事,你應當把墳墓趕快遷走。」當時葉祺並不相信。不久之後全家人都病得很嚴重,於是心中恐懼而趕緊遷移墓地。隔天,傳燈就到了高明寺,隨即在當地建立天台宗的祖庭,風聞而前來學法的人,從四方聚集而來。
傳燈曾經在新昌的大佛之前登座立義說法,大眾都聽到石室之中有天樂響亮和諧共鳴的聲音,一直到說法結束之後才寂靜下來。傳燈曾經著作《淨土生無生論》,融會了空、假、中,一心三觀的義理,闡述發揚淨土法門。又有一篇法語,最是懇切精要,其文曰:
「楊次公(楊傑)曾經說過:『愛不重,不生娑婆,念不一,不生淨土。』對娑婆世界有一個愛念不能放下,則臨命終時必定為此愛念所牽引,何況是有眾多的愛念執著呢?求生極樂有一念不專一,則臨終時必定為此散亂之念所轉,何況有多念的散亂不一呢?所謂的『愛念』,有輕的,有重的,有厚的,有薄的,有正報的,有依報的。如果一一列舉它的項目,則父母妻子、兄弟朋友、功名富貴、詩詞文章、道術技藝、衣服飲食、屋宅田園、山林流泉花草樹木、奇珍異寶古董玩物,實在無法一一數盡。有一念之心不能忘懷,這就是愛念。有一念之心不能放下,這也是愛念。有一個愛念存在心裡,則心念不專一。如果有一念不能專一,那麼就不能夠往生淨土了!」
有人問:「淡薄愛念有什麼方法呢?」回答說:「想要淡薄愛念,無過於專一心念。」又問:「專一心念要用什麼辦法呢?」回答說:「想要專一心念,莫過於淡薄愛念。凡是心念不能專一,都是由於散亂心向外攀緣他物的緣故。心念散亂攀緣他物,都是由於向外追逐境界而使心念紛紛擾擾的緣故。娑婆世界有一個境界,則眾生就有一念執著之心,眾生有一念執著之心,娑婆世界就有一個境界,眾緣和合在心內撓亂動搖,趣向心外奔馳放逸,內心與外境交互的馳逐,紛紛亂亂猶如滾滾的塵沙。因此,想要淡薄愛念執著,則莫若斷除外境,一切的境界皆空,則萬緣自然寂靜。萬緣都寂靜,則自然能夠專一心念。既然能夠專一心念,則愛念攀緣的心就全部止息了。」
又問:「斷絕外境有什麼方法嗎?」回答說:「斷絕外境者,並不是摒除放棄一切的萬有,也不是閉起眼睛而不看事物。而是在當下的境界裡,了知其虛妄不實之性,契入真實的本體,而空去其虛幻的枝末。一切萬法本來不是自己而有的,所以會『有』是因為情執的關係。因此情執在則外物存在,情執空則萬物空。萬法既空,則本性自然地顯現。本性顯現則情念自然地止息。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,並非勉強而得來的。《楞嚴經》所謂的能見之性與所見之外緣,都是妄情想相而成,都是如同幻化於虛空之華,本來一無所有。此能見之性與所見之外緣,原來都是菩提覺性妙淨明體,云何於中有是有非有好有壞呢!
因此,若是想要斷絕外境,則沒有比體悟萬物的虛幻不實更好的方法。體悟到萬物的虛幻性,則情執自然就斷除。情執一斷,則愛念就不會產生,而所謂的『萬法唯心』就顯現了,心念專一的工夫也就成就了。因此《圓覺經》說:『知幻即離,不作方便;離幻即覺,亦無漸次。』妄心一去除,真心自然顯現,這是沒有一點間斷差錯的。功效的迅速,猶如擊鼓即出兵一樣。學道之士,在這個地方應當盡心盡力去下工夫!」
問曰:「淡薄愛念的方法已經聽法師您的耳提面命了,而『專一心念』的方法又是如何呢?」
答曰:「專一心念的方法有三種:一是信、二是願、三是行。求生極樂世界,以切實深信為開始。此必須遍讀大乘經典,廣學祖師的教法。凡是開示闡明淨土法門的書,都應當一一去參究研讀。如此則能了悟:極樂世界原來是我唯心的淨土,不是心外的他方國土;阿彌陀佛原來是我本性的自佛,不是心外的他佛。
第二是修行,修行的法門有二,一是正修、一是助修。正修行又有兩個,一是稱佛名號,二是觀想。稱念名號的,就如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所說,七日執持名號,達到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又分為『事一心』與『理一心』。
如果口裡稱念佛名,心中繫念於阿彌陀佛的名號,如此聲聲相續,心心不亂。假使心念攀緣於外境,即時收攝令其回到佛名。這個必須是要發決定心,斷除對未來的妄想,遠離世間俗事,放下攀緣的散亂心。使念佛的心漸漸增長,從漸漸到持久,由少至多,一日二日,乃至七日,畢定要成就一心不亂的工夫才停止,這就是所謂的『事一心』了!如果能夠如此,則往生極樂世界的淨因已經成就,臨命終時必然有正念,那麼想要親見阿彌陀佛垂手來接引我們往生淨土,也就是確定不移的事了。
而所謂的『理一心』,也沒有別的,只要在『事一心』時,念念之間能夠明了通達,能念佛的心,所念的阿彌陀佛,過去現在未來三際平等,十方世界互相含融,不是空也不是有,沒有自也沒有他,無去無來,不生不滅。現前這一念念佛的心,便是未來往生淨土之清淨世界。念而無念,無念而念。無生而生,生而無生。於無能念所念之間,而精進熱誠地念佛,於一切法無生無滅之際,不昧事相地努力求往生。這就是從『事一心』之中明了『理一心』!
其次,正修行中的第二種:『觀想』,完整的解說就如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中所開示的。所觀的境界共有十六種,其中觀想阿彌陀佛是最重要的。應當觀想阿彌陀佛一丈六尺的身高,作紫磨黃金色的形像,站立在蓮華池上,作垂手接引眾生的姿態。身上有三十二種大丈夫相,一一相有八十種隨形好。這兩種『稱念名號』和『觀想』的正修行,必須要互相輔助而行。凡是行住睡臥之時,則一心稱念佛名,凡是靜坐的時候,則心心觀想阿彌陀佛。經行疲倦了,就坐下來觀想佛,靜坐之後起座,則經行而持念佛號。如果能夠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,修行而不間斷,那麼往生淨土就是必然的事了!
『助行』也有兩種;第一,世間的助行。例如孝順父母,行世間的仁慈,慈心不殺生,圓滿受持種種戒律。一切利益眾生之事,若能回向往生西方,則無非是助道之行。第二,出世間的助行。例如六度萬行,種種的善行功德,讀誦大乘經典,修習各種的懺悔法門。同樣也必須回向往生淨土以資助正行,如此則一切出世間的善行亦無非是淨土之行。
更有一種微妙的助行,那就是每當經歷一切的外緣境界,應當要處處用心。例如見到眷屬,應當把他當作西方的法侶眷屬來想,以淨土法門來開示導引他們,令他們減輕愛念而專一佛念,將來永遠作同悟無生的法侶眷屬。如果生起恩愛的念頭時,應當思惟憶念極樂淨土的法侶眷屬,是沒有情執愛戀的。何不應當得生淨土,而遠離此種貪愛執著。如果生起瞋恚的念頭時,應當思惟憶念極樂淨土的法侶眷屬,絕對不會有衝突惱害,何不應當得生淨土,而遠離此種瞋恨惱害。如果受苦時,當念淨土,無有眾苦,但受諸樂。如果受樂時,更應當憶念西方淨土之快樂,是無止盡無對待的。凡是經歷一切的外緣境界,都是以這種意旨而推廣之,則無論一切的時間處所,無非都是往生淨土的助行。
第三,發願。往生淨土的舟航,要以『信』為船舵,『行』為船隻的竹篙、木槳、桅杆、繩纜,以『願』為風帆。如果沒有船舵,則無有方向指南。沒有竹篙、木槳、桅杆、繩纜,則船隻不能運行。沒有風帆,則不能乘風破浪快速地到達目的,所以在『行』之後要說明『願』。但是願有通別之分,有廣狹之分,還有普和局限之別。所謂的『通』,就如同古來祖師大德所立的回向發願文。所謂的『別』,則各隨自己的意思而發願。所謂『廣』,即是四宏誓願,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願。所謂『狹』,是衡量自己的力量,先求決定往生淨土。所謂『局限』的,例如依照定時的課誦,隨著大眾一同發願。所謂『普』的,是時時發起信願,處處標定心志,決定要往生淨土。但是必須要合於四宏誓願之體,不得擅自任意地立願。如果依此『信』、『願』、『行』三種法修行,必定可以往生淨土,急速得以面見阿彌陀佛。一切的淨土法門,都不外於此三者也!」
傳燈每年都修行四種三昧,自己身體力行率領大眾,精進勇猛修行不懈。曾經註解《楞嚴》、《維摩詰》等經典,每當註疏書寫時,必定披穿受戒的袈裟。傳燈法師前前後後應邀講經有七十多期。年七十五歲,預知臨終的時間已至,親手書寫『妙法蓮華經』五字,又一再地高唱經題,然後安詳地圓寂往生。(法華持驗。淨土法語)
明 古松
古松。山西平陽人,幼年時出家於五臺山的羅 ![]()
明 仲光
仲光。字法雨,號佛石山儂,浙江錢塘戴氏的子弟。母親夢見有僧人以袈裟覆蓋她的身體,後來就生下仲光法師。仲光從小就厭惡葷食腥羶。年十四歲,投靠靜明法師剃度出家。十八歲,受戒於雲棲寺。遊歷參學於各個講經道場,學習天台宗的教觀思想,深入一佛乘的義理。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(西元一五九四年),在金陵參拜了紫柏禪師,親自承受他的授記印可。接著返回武林山,走到十八澗的時候,由於喜好其林木山谷的幽深不凡,因此就在當處誅除茅草堆疊石塊,建構了一個小屋舍。有一天因為耕作掘地,挖得一塊殘缺的石碑,知道是古代的『理安寺』,因此而重新建築之。後來四方的僧人競相聚集而來,而成為一座叢林道場。
仲光法師隨著根機而引導教化眾生,於禪堂之外,另外再開設念佛堂。當時正好憨山德清大師到來,因而與之商訂念佛堂的規約制度,將一天分為十二時,人眾平均而分為六班,每班各六時,經行念佛,禮拜回向。其他班的人員則各個靜坐,隨著聽聞的佛號而跟著默念,或者學習觀想,動中和靜中的修行兩者兼得。
明思宗崇禎九年(西元一六三六年)七月十五日,忽然示現些微的疾病,告訴弟子說:「今日天氣晴朗,我想要到遠方去!」弟子說:「師父生病,想要到那裡去呢?」仲光說:「你認為我生病嗎?」說完就拄著拐杖走出寢室,然後結跏趺坐,集合大眾,交待吩咐後事。正好有蔡居士來到,仲光高興拍手笑說:「居士你正好來為我證明,其他的人則來不及等待他們了!」因而書寫偈頌曰:「一句彌陀五十年,分明掘地討青天。而今好個真消息,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書寫完畢後,轉頭看看左右,然後投下毛筆而往生。(淨土全書。理安寺紀)
明 金童廟僧
金童廟的僧人,不知道他的法名,金童廟位於江蘇常熟的北門。這位僧人每天持著一個板,在街頭巷尾之間打板,然後高聲的唱曰:「無常迅速,一心念佛。」大眾都不認為他有什麼特異的。明思宗崇禎十三年(西元一六四○年)三月,突然向所有的鄰舍告辭說:「好好念佛,老僧去矣!」眾人都不了解其緣故。第二天,僧人在佛前拈香,合掌稱念佛名,然後端身正坐而往生。(淨土約說後跋)
明 海寶
海寶。不清楚他的出身。居住在常州(江蘇武進縣)的天寧寺。相貌甚為樸實,人家和他說話,從不回答一句話,只是微笑而已。殘破的僧服充滿了蝨子跳蚤,有空時則面對佛像席地而坐,上上下下地捉著蝨子,但是都未捉離他的身體。海寶常常募錢買蔬菜豆腐,供養寺裡的僧眾。又聚積受布施的金錢,懇請眾僧誦經禮懺,自己則一心念佛回向,每年都是如此。
明思宗崇禎年間(西元一六二八~一六四三年),翰林學士鄭胙長,邀約海寶法師朝拜南海普陀山,海寶先是答應,但不久又跟他推辭掉了。
鄭胙長起程之後,常常見到海寶在前面的陸地上行走,想要追又追不上。等到登達山頂進入大殿,海寶又在大殿裡面。派人邀請海寶法師一同回去,又不願意。等鄭胙長回到常州郡時,即到寺裡等候海寶法師回來。海寶的弟子說:「師父重病臥床已經一個多月了,昨天才起床呢!」鄭某於是向人敘述海寶法師的神奇特異,常州郡的人因此才恭敬信仰。有一天,海寶自己盤腿端坐,安然地念佛而往生。(淨土晨鐘)
明 大雲
大雲。字萬安,俗姓郭,仁和人(浙江杭州)。出家於永慶寺,受具足戒於雲棲寺。平日居住在北郊,專志修習淨土行業,前來依止的人非常多。因此募款建立吉祥寺,殿宇寮房燦然興盛,於是成為一個大叢林。其共住的規約,完全依秉雲棲寺的制度。不久,示現些微的疾病,於是斷絕飲食,專意稱念佛號。如是經過一個月,其間如果有人前來探視他的,大雲就說:「阿彌陀佛不憶念,想念我作什麼?」臨命終時,告訴弟子智經說:「為我灑掃乾淨,阿彌陀佛來迎接我了!」說完就端坐念佛而往生,時年五十九歲。(靈峰宗論)
清 無名僧
無名僧,居住在湖廣黃州,專門持念阿彌陀佛,晝夜從不停止。無論見到什麼,都念阿彌陀佛。明思宗崇禎十六年(西元一六四三年),黃州總兵黃鼎,守護黃州城,無名僧大聲念佛擾亂黃鼎帶兵,因此命令人把他捉起來。正好張獻忠攻打黃州城,無名僧被捉坐在城上,半夜裡高聲地念佛,吵得官兵不得睡眠,眾人恨之,把他綁起來從城上丟到城牆下。可是不久又見到他在城上念佛,如是丟下又上來有四次之多。每次從東邊的城牆丟下,就從西邊的城牆上來,從南城丟下,就從北城上來,總兵聽到這件事之後,才開始恭敬禮遇他。
有一年,黃州鬧大饑荒,人們相殺而食。一日,無名僧走出城外,饑餓的城民持刀來乞求他捨身,無名僧脫下衣服告訴眾人說:「等我念佛一千聲之後,就可以吃我!」當念到三百聲的時候,眾人等不及急而想殺他,此時忽然有神兵從空中而來,饑民因此驚怖四散逃回城裡,卻看到無名僧已經在城中了。
當時山中有獵人捕得一隻大老虎,無名僧想要買來放生,獵人要求三十金,僧人只有四金而已。獵人說:「如果你能夠捉住老虎的耳朵,提起來繞行三圈,我就把老虎給你。」無名僧於是囑咐老虎,然後捉著老虎的耳朵繞行三圈,獵人因此把老虎放了。可是老虎卻跟著無名僧不肯離去,僧人於是和老虎一同前往黃麻山的金剛洞居住。巡撫盧象昇,率兵經過黃州時,到山裡拜訪他,想要見老虎。無名僧一說話叫牠,老虎就把頭探出窗外。盧巡撫想要見老虎的全身,老虎於是大叫地跳出來。盧巡撫因此而向無名僧拜師送禮,自稱是弟子,然後才離去。無名僧有一天行走於街道中,見到一隻雞,他高聲地念佛,那隻雞也隨著音聲而唱。
清世祖順治七年(西元一六五○年),無名僧想要到武林山,路過白門(江蘇江寧縣)這個地方,寄居於秦淮河旁的房子。那天正好是端午,無名僧看見遊河的船中有錢姓儒生,是他的弟子,因此就呼叫:「錢某,阿彌陀佛!」錢某於是上岸拜見無名僧。僧問錢某的同遊朋友,知道是某某人,因此放聲大哭說:「眾生以苦為樂,乃如此啊!」錢某懇切的請示修行的要旨,無名僧說:「一心念阿彌陀佛!」又說:「我走之後,你有什麼疑問,可以問覺浪禪師,此是明眼人!」無名僧後來不知所終。
覺浪,名道盛,曾經主持金陵天界寺,杭州崇光寺等諸處道場,禪門的宗風因此大振。(淨土晨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