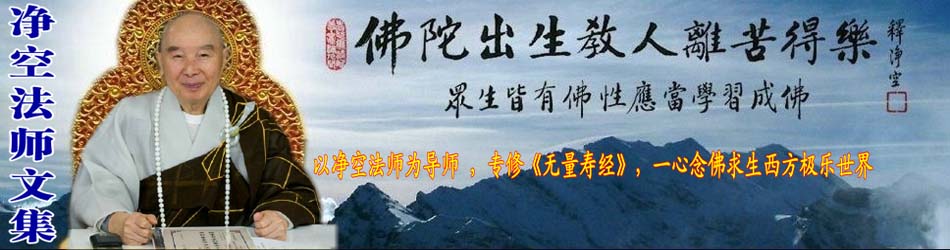淨土聖賢錄易解卷6-2
清 明宏
明宏。字梅芳,杭州人,年將二十歲,父親為他娶媳婦,於是逃家而去。母親痛哭,因此雙眼失明。後來父母相繼過世。明宏才在紹興柯橋的彌陀庵剃度出家。出家後即到處參訪,學習天台宗的教觀,坐禪而有所省悟。後來閱藏於天台山的萬年寺,時間久了之後,兩眼因疲勞而受損,自己說:「這就是我違背雙親慈憫愛念的果報啊!」從此以後一心念佛,無論寒暑從不間斷。自己曾經說:「我因為眼睛失明,卻得到大利益。」平時一缽一杖,沒有固定的居處,凡是所得到供養,隨即布施給貧乏困苦的人。思齊實賢大師與明宏為友,曾經告訴明宏說他決定往生淨土,他說明宏法師有三真:真解脫、真乾淨、真精進也!
清雍正五年(西元一七二七年)九月,思齊實賢大師於梵天寺,起念佛七的法會,招攬明宏加入蓮社,當時明宏患痢疾,但是依然精進持念佛名,沒有絲毫的懈怠。念佛七結束後,前往無錫的齋僧館,病情又轉重。有一天,告訴所有的施主,約定明天要往生。大眾依照約定的時間來到,明宏即起坐站著念佛,然後合掌而往生。(思齊大師遺稿)
清 明德
明德。字聖眼,俗姓馬,杭州海寧人。四歲,出家於梵天寺。十六歲,剃度。個性孤僻,不喜好世間俗務。等到三十六歲時,想要尋訪律師求戒,忽然得氣喘病,日益嚴重。有徒孫名一葦,延請數位僧人在寺內開念佛堂,思齊實賢大師也在其中。念佛堂的左邊,即是明德的臥室,每天聽到大眾念佛聲,總是默默地隨著憶念。不久自知時至,命令一葦請眾僧到他的床前,一齊同聲唱念佛號,過一會兒,叫大眾停止,告訴實賢大師說:「願師父開示。」賢公開示說:「你應當捨盡萬緣,一心念佛。想要了生脫死,在此一時,更加應當著力用功。」明德於是和大眾一起持名念佛。又發四宏誓願,語調心意極為懇切。到了半夜,念佛聲才停止,大眾才一舉聲稱念觀音聖號,明德即轉身垂下雙眼而往生。當時為清世宗雍正七年(西元一七二九年)十二月二十六日。(思齊大師遺稿)
清 實賢(蓮宗十一祖)
實賢。字思齊,號省庵,江蘇常熟一帶時姓人氏的子弟。從小不吃葷腥。出家後,參究念佛者是誰,有所省悟,說:「我的夢醒了!」後來閉關於真寂寺,其間三年,白天閱讀藏經,晚上課誦佛號。曾經到
山禮拜阿育王塔的佛陀舍利,在佛陀涅槃日,大大地集合僧俗二眾,廣修供養。在佛前燃指,發四十八大願,於是感得舍利放光。又作《勸發菩提心文》,以激勵四眾弟子,讀誦的人多為之感動流淚,其文章曰:
「曾經聽說入道之門,以發心為首要。修行的急務,以立願為最先。願如果立,則眾生可度,心如果發,則佛道可成。如果不發廣大心,立堅固願,則縱然經過塵點劫,依然還在輪迴。雖然有在修行,總是徒勞辛苦。《華嚴經》云:『忘失菩提心,修諸善根,是名魔業。』忘失菩提心尚且如此,何況尚未發心呢?由此可知,想要學習如來一乘的佛法,必定先要完整地發起廣大的菩提願,不可以稍有遲緩也!
然而發心立願的差別,其相貌乃有多種,現今為大眾簡略地說明之。其相貌有八種,所謂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是也。世間有一些修行人,不向內參究自心,只知向外追求奔馳。或者追求利養,或者喜好名聞,或貪圖現世的欲樂,或者期望未來的果報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邪』。
既不追求利養名聞,又不貪圖欲樂果報,只是為了了脫生死,為了追求無上的菩提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正』。念念上求佛道,心心下化眾生。聽說佛道長遠,不生退怯之心;明知眾生難度,不生厭倦之想。如同高登萬仞之山,必定要到達其頂。如上升九層之塔,必定要爬到其顛峰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真』。
有罪惡而不懺悔,有過失而不去除,內心污濁外現清淨,開始時精進最後又懈怠。雖然也有好心,卻為名利之所夾雜,雖然也修善法,但為罪業之所染污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偽』。
眾生界盡,我願方盡;菩提道成,我願方成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大』。
觀三界火宅如牢獄,視生死輪迴如怨家,只期望自度,不想要度人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小』。
若於心外見有眾生可度,以及有佛道可成,功勞得失不忘,分別知見不除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偏』。
知道自性是眾生,因此願意度脫。了解自性是佛道,因此願意成就。不見有一法離心之外還能存在。以虛空之心,發虛空之願,行虛空之行,證虛空之果,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如是發心,名之為『圓』。
知道這八種相貌差別,則知道審察分別,知道審察分別,則知道要去除或選取。知道去除或選取,則可以發心。如何審察分別呢?那就是說,我所發的心,於此八種之中,為邪?為正?為真?為偽?為大?為小?為偏?為圓?如何去除或選取呢?那就是去邪、去偽、去小、去偏。取正、取真、取大、取圓,如此發心,才可以名為是真正的發菩提心啊!
然而此菩提心,是一切善法中之王,必定要有因緣,才可以發起。現在討論其因緣,大略有十種,那十種呢?一者,念佛重恩故。二者,念父母恩故。三者,念師長恩故。四者,念施主恩故。五者,念眾生恩故。六者,念生死苦故。七者,尊重自己的靈性故。八者,懺悔業障故。九者,求生淨土故。十者,為令正法得以久住故。
什麼叫作念佛重恩的因緣呢?那就是說,我釋迦如來,從初發心開始,為了我等眾生之故,行菩薩道,經於無量劫,備受種種的痛苦。當我們造業的時候,佛則慈悲哀憐,巧設種種方便教化,而我等愚痴無智,不知信受奉行。等到我們墮落地獄了,佛陀又心生悲痛,想要代我受苦,然而因為我們業障太重,不能救拔。我們生於人道之中,佛陀以種種方便,令我們種下善根,生生世世,追隨憶念著我們,心念沒有暫時的捨離放棄。當佛陀出世度化眾生的時候,我們還在沈淪生死。現今我們得到人身,佛陀卻已經滅度了。到底是因何罪過而生於末法,是何福報而得以出家。到底是何障礙而不能見到佛陀的金身,是何幸運而得親見佛陀的舍利。經過如是的思惟,如果我們過去不曾種下善根,何以能夠得聞佛法,不能聽聞佛法,那裡知道常常蒙受佛陀的恩澤。此恩此德,像山丘一樣地高大而難以比喻。如果不是以發廣大心,行菩薩道,建立佛法,度化眾生的方式來報答,那麼縱使粉身碎骨,也難以報答佛陀的重恩,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一個因緣啊!
什麼是念父母恩的因緣呢?慈悲的父母,生我之時極為勞苦,十月懷胎,三年哺乳,才能夠長大成人。本來指望我接續承繼本有的家風,傳宗接代供養祭祀。如今我等既已出家,濫稱佛門的弟子。既不能供養父母美味的飲食,也不能祭祀打掃祖先的墳墓,父母在生時不能奉養他們的口味和身體,死後又不能引導他們的神靈往生善道。於世間法對父母是大損失,於出世間法對父母又無實質的利益。世間、出世間兩方面都有過失,那麼將來的重罪也就難逃。經過如是的思惟,也只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,十方三世普度眾生才可以報答父母恩。那麼不只一生的父母,即使是生生世世的父母,也都能夠蒙受拔度救濟。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父母,即使是人人的父母,也都可以超昇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二個因緣啊!
什麼是念師長恩的因緣呢?父母雖然生長養育我的色身,若是沒有世間的師長,則不能知道世間的禮義。如果沒有出世間的師長,則不能了解出世的佛法。不知禮義廉恥,則同於異類畜生。不了解佛法,則何異於世間俗人。如今我等粗淺地知曉禮義廉恥,約略地了解出世佛法,袈裟得以披體,戒品能夠沾身,此種重大的恩德,皆是從師長而得來。若我們僅僅追求小乘之果,則只能自利不能利人。如今應當實踐大乘,普願利益一切世人,則世間、出世間二種師長,都可以蒙受利益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三個因緣。
什麼是念施主恩的因緣呢?我等現今每日所用的資具,並非自己所有。二時食用的粥飯,四季穿著的衣裳,疾病所須的醫藥,色身口舌所花費的,這些都是出自他人之力,而把它拿來為我所用。別人是竭盡體力親自耕作,還尚且難以餬口;我則安穩地受人飲食,心裡猶不滿意稱心。別人是辛勤地紡織裁縫,仍然困苦艱難;我則是衣服充足有餘,哪裡知道愛惜。別人在簡陋的柴門茅屋之內,紛紛擾擾地度過一生;我則是在高大的殿堂廣闊的庭園之間,優遊自在地度過年歲。以別人的努力勞苦而供給我安逸快樂,內心覺得很安然嗎?將他人的利益來長養自己的色身,這個順乎道理嗎?如果不是悲智雙運、福慧二嚴,令布施的檀信均沾諸佛的恩德,讓一切的眾生受到佛法的賜益,那麼就算是一粒米、一寸絲,將來也有酬償的分,地獄餓鬼這些惡報,如何能夠潛逃呢?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四個因緣。
什麼是念眾生恩的因緣呢?那就是說,我和眾生,從無始劫以來,世世生生,互為父母,彼此都有恩德。今日雖然隔了幾世昏迷不知,彼此互相不認識,但是以道理來推論之,難道不應該為他報答效力嗎?現今披毛戴角的眾生,哪裡知道我在過去生中,不曾經是他的兒子呢?現今那些蠕動紛飛的有情,哪裡知道他過去不曾經是我的父親呢?至於那些高聲呼號於地獄之下,宛轉流浪於餓鬼之中,痛苦傷心有誰能知,飢餓虛弱又要向誰投訴呢?這些事情我現今雖然不能見不能聞,而他必然希望能求得我們的拯救拔濟。如果不是經典就不能陳述這些狀況,不是佛陀也不能說出這些事實。那些邪知邪見的人,哪裡有能力知道這些六道因果的真理呢!因此菩薩觀看螞蟻,皆是過去的父母、未來的諸佛。常常思惟要利益眾生,常常憶念要報答其恩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五個因緣也!
什麼是念生死苦的因緣呢?我與眾生,從無始劫以來,常在生死,未得解脫。或者人間或者天上,或在此界或在他方,輪迴出沒千門萬端,剎那片刻上下升沈。晨朝才出了黑門,夜暮又愚痴地回來;才暫時脫離鐵窟,馬上又造業而入。登上刀山,則全身體無完膚;攀爬劍樹,則方寸的皮肉都割裂。熱鐵不能除飢,吞之而肝腸盡爛;銅汁哪能止渴,飲之則骨肉都糜。以銳利的鋸子分解之,可是斷了又馬上接續而再鋸,業風一吹,則死了又復生而受苦。在猛火焚燒的城中,何忍聽到悲慘的哭號。於熱火煎熬的鐵盤裡,又有誰能夠聽聞到他苦痛的聲音。開始冰凍凝結,則膚色猶如青蓮的花蕊;冰凍至極血肉裂開,形狀就像紅色的蓮華綻開。在一夜之間,地獄裡的死生已經經過萬遍;地獄片刻的痛苦,在人間已經過了百年。頻頻麻煩獄卒來疲勞的用刑,可是又有誰相信並記得閻羅王的教誡呢!
受刑的時候知道痛苦,雖然悔恨但也沒法追回過失;脫離刑獄時又忘了痛苦,其所作的惡業依然如故。虛妄的心沒有一定的主宰,就如同買賣的商人處處奔馳;不斷輪迴的色身並無一定的形體,就好像換房子一樣地頻頻遷移。即使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之數,也難以比喻我們曾經輪迴過的色身;即使像四海波濤之大,也難以計算我們生生世世以來生離死別所流之淚。如果把我們過去輪迴的枯骨堆積起來,早就超過了高山;累積起來無量無邊的死屍,也多於廣闊的大地。過去如果不曾聽聞佛法,此事又有誰能見能聞;如果不曾看過佛經,這個道理如何能知能覺。若是依然如從前一樣地貪戀,仍舊如昔日一般地癡迷,只恐怕萬劫千生,一錯百錯。人身難得而易失,良辰易往而難追。輪迴的道路迷迷茫茫,別離比相聚的時間還長久,三途的惡報,終究還是要自作自受。生死輪迴真是痛苦難言,又有誰能夠來代替呢?經過如是的思惟,因此我們應當斷生死之流,出愛欲之海,自他兼濟,彼岸同登,無量劫以來殊勝的功勳,就在此一舉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六個因緣。
什麼是尊重自己靈性之因緣呢?那就是說,我們現前當下的一念心性,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。為何世尊無量劫以來,早已成等正覺;而我等依然昏迷顛倒,猶是凡夫。又世尊具有無量的神通智慧,功德莊嚴;而我等但有無量的業障煩惱,生死纏縛。心性雖是同一的,但是迷悟卻有天淵之別。譬如無價的摩尼寶珠,淹沒在淤泥之中,而被視同無用的瓦礫,不知加以愛惜珍重。因此應當以無量的善法,對治種種的煩惱,修行的德業有功,本性的妙德才能顯現。就如摩尼寶珠被洗滌清淨,懸掛在高幢之上,廣闊通達光明照耀,輝映覆蔽一切萬物,可以說是不辜負佛的教化,不屈辱自己的靈性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七個因緣。
什麼是懺悔業障的因緣呢?經典云:『犯一個突吉羅小罪,如四天王的壽命五百歲的時間墮地獄中。』突吉羅的小罪,尚且獲得此種果報,何況是犯重罪,其果報真是難以言喻。如今我等日用平常之中,一舉一動,恒常違背戒律,一頓飯一飲水之間,頻頻觸犯尸羅(戒律)。一日之中所犯的過失,本來就應當是無量無邊,何況是終身和無量劫以來,所引起的罪業,更是多得不可言說了!如今且以五戒來說,十個人有九個違犯,少有發露懺悔,大多覆藏不言。五戒名為優婆塞戒,尚且不能具足受持,何況是沙彌比丘菩薩等戒,那又不必說了。如果不是愍念自己又愍念他人,慈悲自己也慈悲他人,色身與口業都至誠懇切,聲淚俱下,普與眾生,求哀懺悔,否則即使是經過千生萬劫,也惡報難逃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八個因緣。
何謂求生淨土的因緣呢?在此娑婆國土修行,想要道業進步也很困難;而那些往生淨土的人,想要成就佛道卻很容易。因為容易,所以一生就可以達到;因為困難,即使累劫也未能成就。因此往聖先賢,人人都趣向極樂;千經萬論,處處都指歸淨土。末法的五濁惡世想要修行,無過於此淨土法門。然而經典說少善根福德不能往生,多福德善根才能到達。若是說到多福德,則莫若執持名號;談到多善根,則莫若發廣大心。暫時執持聖號,勝於布施百年;一發廣大道心,超過修行歷劫。因為念佛,本來就是期望要作佛,若是廣大的菩提心不發起,則雖然念佛又有什麼用。發菩提心,原本就是為了要修行,如果不往生淨土,則雖有發心但容易退失。如果能夠播下菩提種,以念佛為耕田之犁,那麼道果自然得以增長。乘著大誓願的船,入於前往淨土之海,則西方決定往生。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九個因緣。
什麼是為了令正法久住?我們釋迦世尊從無量劫以來,為我等故,修菩提道,難行能行,難忍能忍,因地具足果地圓滿,終於成就無上佛道。既已成就佛道,廣度眾生的教化因緣又已結束,入於寂滅究竟涅槃。正法像法,皆己滅盡,只剩下末法,有教法而無證悟的聖人。邪正不分、是非莫辨。都是在競爭人我高下,盡是在追逐利養名聞,從不知道佛是何人,法是何義,僧是何名。衰微殘敗到如此的地步,實在不忍言之。每當思惟到這裡,不覺傷心淚下。我為佛子,不能上報佛恩。內無益於己,外無益於人,生無益於當時,死無益於後世,所謂罪大惡極的人,不是指我那是指誰呢!
因此痛不可忍,無計可施,頓時忘了自己的粗淺鄙陋,忽然發起廣大道心,偕同諸位善友,同到道場,為了懺悔罪業,於是建立此法會。發四十八之大願,願願度化眾生,以百千劫的深心為期誓,心心想要作佛。盡此一生之身形,誓願歸向極樂世界。既已登上九品蓮華,再回入娑婆廣度有情,以使得佛日重新增輝,法門再得闡揚,僧眾之海澄清於此世界,人民蒙受教化於東方,好的劫運更加延長,使得正法得以久住。此則是區區如我的真實苦心,這就是發菩提心的第十個因緣。
如是十個因緣都認識,邪正真偽大小偏圓八種法都知道,則有門路可以趣向,有目標可以開發。唯願大眾憫念我的愚痴和誠心,悲憐我懇切的志向,同立此願,同發此心。未發心者今發起,已發者令增長,已增長者令其相續。不要畏懼困難而退怯,切勿視為容易而輕浮,不可欲求快速而不長久,不應懈怠而無勇猛,不要因為愚鈍而無心修行,不可以根器淺薄而自輕以為無分。譬如種樹,種久則根淺而日深。又如磨刀,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。豈可因為根淺而不種,任其自己乾枯。豈可因刀鈍而不磨,將它放棄而不用。
如果以修行為苦,則不知懈怠更是苦。修行是暫時勤勞,而得到長久劫的安樂。懈怠是偷安一世,可是卻受苦多生多世。何況能以淨土為舟航,則何必憂愁會退轉。又以無生為忍耐之力,何必思慮艱難困苦,千萬不要說一念是輕微的,不要說虛浮的願力是無益的。心只要真則事情就會實在,願只要廣則修行就會深入。虛空非大,心王為大,金剛非堅,願力最堅,大眾如果真的能夠不捨棄我的這番話,則菩提眷屬,從此聯姻,蓮社宗盟,自今諦好,我所願的是大家能同生淨土,同見彌陀,同化眾生,同成正覺。」
實賢法師晚年居住於杭州的仙林寺。清世宗雍正七年(西元一七二九年),創立蓮社,作文章為大眾立誓,以終其身命為期限。將每日的功課分為二十分,十分持名念佛,九分作觀想,一分禮拜懺悔。他曾開示修禪者念佛的偈頌曰:
「一句彌陀,頭則公案,無別商量,直下便判。如大火聚,觸之則燒。如太阿劍,攖之則爛。八萬四千法藏,六字全收。千七百隻葛藤,一刀齊斷。任他佛不喜聞,我自心心憶念。請君不必多言,只要一心不亂。」
清雍正十一年(西元一七三三年)十二月八日,告訴弟子說:「明年四月,吾將去矣!」於是閉關在一室內,每日念佛名十萬聲。次年四月十二日,告訴大眾說:「我從這個月初一以來,一再地見到西方三聖,大概是要往生了吧!」於是書寫偈頌向大眾告辭,第二天(十三日),斷絕飲食,收攝眼光端身正坐,五更時(清晨三~五時),沐浴更衣。十四日,將近中午,面對西方寂然而坐。前來送行的人成群而至,此時實賢忽然張開眼睛說:「我去了就來。生死事大,各自淨心念佛就可以了!」說完就合掌連續稱念佛名,然後往生,時年四十九歲。(思齊大師遺稿。僧素風述)
清 明悟
明悟。字丙元,黃州(湖北黃岡縣)人,年輕時出家於仁壽庵,受具足戒於歸元寺,之後訪諸方的善知識,了悟心法,受印可於皋亭佛日寺的璿鑑和尚。曾經主持吳江的長慶寺,蘇州的珠明寺,石門的崇慶寺,皋亭的佛日寺等諸寺院,最後歸老於蘇州的龍興寺。晚年精修淨土法門,日夜從無間斷。清高宗乾隆十七年(西元一七五二年)正月九日,正好寺裡齋天,明悟告訴大眾說:「諸位大德好好安住,我在上元節(正月十五日)以前就要去了!」到了十四日,作偈頌曰:「山僧年望七,諸緣事已畢,自入涅槃門,不露真消息。」於是取熱水盥洗沐浴並更換新衣,命令大眾稱念佛名,到午時安然入寂往生,時年六十九歲。(僧鶴峰述)
清 德峻
德峻。字廣聞,一字蒼巖,蘇州人。出家於蘇州城中的妙隱庵。到處參訪諸方的善知識,承襲曹洞宗的法脈,住在杭州回龍的真寂寺。回到蘇州後閉關於盤溪的小靈隱寺。先後數年之中,精進修行淨土法門,曾經在禪定中,兩度見到阿彌陀佛。出關後,因而建造丈六的阿彌陀佛像,刻印天如禪師的《淨土或問》,引導眾人念佛。時常應大眾的邀請,施放瑜伽燄口,常常有明顯的感應。每次得到供養的錢,從未開封來看,而把這些所藏的金錢財物,拿出來修造種種的佛事。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(西元一七六三年)九月,稍微有氣喘的疾病。召集所有的學生徒弟,環繞著稱念佛號連續七日。七日後的午後,命令大眾到大殿焚香,然後沐浴更衣,端身正坐稱念佛名而往生,享年八十五歲。(僧鶴峰述)
清 聞言
聞言。字超然,俗姓費,嘉興(浙江)桐鄉人,年幼時即不喜食葷腥,喜歡盤腿靜坐。七歲時,入於靈隱山的祇園庵出家。平日為人淳厚樸實,受具足戒於雲林寺的碩揆志禪師,日夜蒙受提攜策勵。聞言曾經說:「某甲根器愚鈍,不善於參究禪法,只知道念佛而已!」碩揆志禪師說:「念佛亦可了生死!」聞言依教奉行,精嚴奉持戒律威儀。二六時中,只有一心持念佛名,從不過問其他的事。清高宗乾隆二年(西元一七三七年)六月二日,忽然召集徒眾,說:「我要走了,你們念佛送我。」即說偈頌曰:「吾年七十七,世緣俱已畢,坐斷兩頭關,得個真消息。且道如何是真消息呢?」然後合掌,端坐而往生。(雲林寺志)
清 道徹
道徹。浙江錢塘人,出家於半山嶺的安隱寺。最初參訪崇福寺、高旻寺的諸位長老,發明本有的心性。後來專修淨土法門。居住在杭州北門外四十里打飯橋的文殊庵之中,約制時期準備閉關。室內沒有多餘的東西,只有一張桌子一個床舖而已。才經過幾日,得疾病,非常嚴重,自己振奮說:「念佛正是為了生死,怎麼可以因為疾病而中斷呢!」於是持念佛名更加懇切。不久之後有金光照室,光中有佛為他摩頂,疾病突然痊癒。後來獲得念佛三昧,行住坐臥之中,毫無其他的妄念。如是閉關念佛經過三年,在三月十五日出關,升座說法之後,告訴大眾說:「我將在七月十五日以後西歸,你們可以來相送。」
到了那一天,大眾都聚集而來,道徹正好設盂蘭盆會。大眾都到齊的時候,提起前些日子說要往生的那件事,道徹說:「是有這件事,但是你們可以先休息,稍待一下。」第二天,道徹迎請他所熟悉的崇福寺僧人,把庵中的住持席位交待給他。又過一天,設齋告別大眾。正午的時候,入坐龕中,閉目端坐而往生,不久之後又甦醒過來,告訴大眾說:「與諸君遠別,難道可以不說一句話。娑婆之苦,不可說,不可說。極樂之樂,不可說,不可說。如果你們還記憶懷念著我,只要念阿彌陀佛,不久就可以相見,錯過此生,輪轉於生死長夜,痛哉!痛哉!」說完之後就坐化往生,時年四十八歲,當時為清高宗乾隆十九(西元一七五四年)。(僧旅亭述)
清 成註
成註。字杲徹,俗姓郭,徐州(江蘇)銅山人。少年出家,年二十歲,受具足戒於寶華山。受戒後遍參諸方的善知識,承受法脈於天童寺的石吼徹公。後來專修淨土法門。清高宗乾隆十二年(西元一七四七年),居住在蘇州的獅林寺。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視,駕臨其寺院,賜名為『畫禪』。成註每日率大眾四次聚會念佛。往往在蠟燭燒完香煙燃燼,大眾都一一散去時,而成註依然念佛聲不絕。時常應大眾的邀請施放瑜伽燄口,所得到的供養,則交給監院,充當修造寺院的費用。沒多久,殿堂煥然一新,日日恢復其舊觀。成註每日半夜,都修大悲懺法,從不睡臥床席。有一天,正在持念佛名,一不小心木魚掉落在地,忽然有所省悟。從此以後,隨口說偈頌,好像宿世曾經修習一樣。
成註曾經開示大眾說:「腳蹋無生路,四面何回互。推出眾人前,分明絕舉揚。本來真面目,萬事皆具足,觸著與磕著,處處超佛祖。更有念佛親,西方勝境真。蓮胎保養處,不隔一毫塵。若人達此意,不勞向外尋。業識消磨盡,往生即此心,華開親見佛,萬象盡回春。」如果有居士問佛法者,則曰:「娑婆苦,何不隨我往西方去呢!」清乾隆三十四年(西元一七六九年)四月,得下痢的病,臥病有一陣子。有一天,召喚侍者來面前說:「扶我起來坐著。」又要了一些橘餅湯來喝,然後正念而往生,時年七十三歲。(畫禪寺雜錄。僧宏通述)
清 了庵
了庵。不清楚他的出身。早年曾經到處參訪叢林,非常用心地參究,晚年則修行淨土法門。後來到和口,安住在棲隱寺。當地的居士嚴氏買田園供養他,不久之後,得疾病,告訴嚴氏說:「可以送我回江南。」嚴氏於是準備舟船,將他送到金山,了庵於是又回到江寧的某寺院。有一天,自己堆積木柴於庭院,坐在柴堆上面,不斷地稱念阿彌陀佛。召喚大眾舉火燃燒,大眾沒有答應。了庵又催促大眾,於是有人拿一炷香給他。了庵把香拿到鼻間吹之,突然火苗從鼻子而出,燃燒了整個面門,皮肉片片脫落,此時念佛聲依然不停,而火又更加地熾盛。大眾在隱隱約約之間聽到念佛聲向西方的虛空而去,過一陣子才消失。了庵自己遺囑交待他的徒弟把骨頭磨成粉,餵食江裡的魚,以結淨土之緣,徒弟們依照他的指示而行。(僧旅亭述)
清 實定、際會
實定。字聞學,俗姓張,松江上海人。年二十多歲,出家於天台山的萬年寺。遍參諸方的善知識,啟發明瞭心法的大要。不久之後主持天目峰的禪原寺。晚年到了蘇州,住在文星閣,曾經說:「達到心地本源之人,功行尚未齊等於諸佛。如果能夠得生淨土,果地的功行才能夠圓滿。」因此常常提倡念佛法門,並著作淨土詩一百零八首。又說:「諸佛的法身,含裹十方世界,經云:『云何是中更容他物。』應當直下去超越種種的限量,遠遠地斷絕去來之相,是心作佛,是心是佛,念念佛出世,念念佛滅度,念念無生,念念往生,頭頭上明白,物物上顯現,總是一句阿彌陀佛,方是真實的念佛人也!」
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(西元一七七七年),回到江陰(江蘇)的香山寺。十二月,得疾病。到了第二年正月三日,已經病了七日了。清晨,向弟子說:「那一日立春呢?」弟子回答:「四日後。」又問:「今天是什麼日?」答:「甲子日。」實定說:「今日好!」於是坐起來,交待後事完畢之後,就枕而臥。到了黃昏,忽然坐起來,呼喚大眾前來,命令準備熱水,一再地洗手,連續不斷地稱念阿彌陀佛。大眾請他說偈頌,於是口說偈頌曰:「繼祖傳燈接虛響,開堂說法鬼打鑼。鼻孔今朝拈正了,蓮華池上見彌陀。」念完偈頌後,寂然地坐著,大眾呼喚他,早已往生了!時年六十七歲。
實定嗣法的徒弟際會,字旅亭,也修念佛三昧。臨命終時作偈告別大眾,吉祥而往生。(二林居後集)
清 實圓
實圓。松江人。年少即有出世的志向。十八、九歲時,在父母將要為他娶妻的前幾天,於半夜裡逃到一個寺院。請求住持為他剃髮,之後隨即到寶華山,受具足戒。其家人向官府控告為他剃度的僧人,官府請僧人追尋實圓的蹤跡,實圓於是把僧服交回,向父母說:「我的頭髮已經剃除,來不及了。」他的父母於是把他關在一個房間內,實圓每日時常打坐,不吃也不睡。父母不得已,乃答應他出家。松江城有僧人設關房,拜《華嚴經》,尚未完成即往生,實圓代為拜經以滿其願。後來到金山寺,行般舟三昧,修行滿一百日。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(西元一七六○年),居住在常州天寧寺,入念佛堂,日夜唱念佛名而不停止。乾隆二十八年(西元一七六三年)三月,示現些微的疾病,集合大眾唱念佛名,把所有的錢拿來供僧。經過三日,自己沐浴後,穿著整齊的僧服袈裟,隨大眾入念佛堂,跏趺而坐,安然地念佛而往生。(僧正琦述)
清 恆一
恆一。字聖學,俗姓沈,常州(江蘇)武進人,出家於穹窿的茅蓬。最初參訪揚州的高旻寺。後來學習天台宗,通達天台的教觀。曾經住在蘇州的文星閣,得到咳血的疾病。於是離開前往杭州半山的顯義院。當他疾病很嚴重的時候,自己預定日期設置齋筵,辭別所有的同參道友,然後唱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而往生。
恆一曾經說過某庵有一僧人,行為放蕩不持戒律,恆一法師和其他一同受戒的朋友規勸他,但是不聽。不久之後此僧得病很嚴重,於是召請他同戒的戒兄說:「我不聽您的話,所以有如此的結果,如今要怎麼辦?」其戒兄說:「西方阿彌陀佛,有本誓願,即使是造業的眾生,十念念佛,都能夠蒙佛接引,你能相信嗎?」僧人說:「信!但是體力不支,怎麼辦?」其戒兄說:「沒有關係!」於是為他設置佛像於床的西邊,叫他雙眼注視勿動。然後點燃鑪香,為他唱念佛名,並捉著病人的手,令他仔細諦聽。如是經過三個晝夜之後,病者忽然坐了起來,謝謝他的戒兄說:「蒙佛接引,得以中品往生了!」然後舉手致意而往生。(僧淨雲述)
清 慧端
慧端。不清楚他的出身。居住在杭州的理安寺,每日課誦佛名數萬聲。後來居住在浙江紹興的善福庵。有一天,邀請同參的僧人澄谷,與其他的僧人五、六人,到善福庵裡念佛。那天太陽才剛到了正午,慧端忽然舉手高唱數聲佛號,然後屹立不動而站著往生,時年二十多歲。(僧澄谷述)
清 法真
法真。字朗如,瑞州(江西)高安人。得度於灌溪元文和尚。受具足戒之後,遊方參學到了嶺南,其中居住在丹霞最久。平時潛心於淨土法門。有一天,偶然與禪者談論到『無』字公案,於是生起疑情並在心中蘊釀了很久,有一日突然豁然開朗有所省悟。於是前往海幢寺,禮拜正目老人,兩人的機鋒話語相互契合,於是受到記別印可。清高宗乾隆二十年(西元一七五五年),大眾迎請他主持海幢寺,提倡禪宗一乘,並兼宏淨土法門。晚年,辭去寺院住持之事,閉關於寺院東邊之旁,專門持念佛名,無論寒暑都不懈怠,如是經過八年。曾經有偈頌說:「百八輪珠晝夜提,芙蕖(蓮華)漸漸出深泥。輪珠擲卻芙蕖放,古佛元來不在西。」
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(西元一七七三年)九月初,示現些微的疾病。十一日黃昏,召集弟子囑咐後事。次日午時,集合大眾唱念佛名,香燒過兩寸多的時候,自己舉念《小淨土文》,未過一半即往生。(僧杲堂述)
清 佛安
佛安。字誓願,蘇州人。年三十多歲時,鄰居有人殺豬,取出其五臟六腑,其中有『曹操』兩個字,於是驚怖恐懼而發心,前往上津橋的天竺庵出家為僧。後來住在北濠的大王廟,每日以念佛為功課。如果有人供養錢,則買香華來供養佛,並贖救魚鳥來放生。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(西元一七七六年)三月,得疾病,派遣徒弟前往獅林寺,請僧眾禮拜淨土懺三天,並施放瑜伽燄口一壇。等三日期滿後,第二日設齋筵召請客人前來與之辭別,並稱念佛名,其徒眾在一旁唱和。念了三炷香之後,已經到了中午,佛安說:「我走了!」然後端坐而往生。
佛安平日偶爾會作詩偈,勸人回向往生淨土。其最後有詩云:「西方世界妙蓮臺,觀裡分明一朵開。赤白青黃無異色,心心唯願見如來。」又說:「莫道西方路正遙,只今彈指上金橋,彌陀接引微微笑,讚爾娑婆戒行高。」(僧修學述)
論曰:「佛法傳入中國,由漢代到晉朝,多以傳述經典解釋義理為先。到了遠公,才建立『白蓮社』,修習念佛三昧,自利利人。後來凡是說到淨土法門者,都以廬山遠公為歸向。而達摩祖師西來,直指人人本心;曹溪六祖說法,簡別輕斥淨土,此乃是禪宗最上乘的一種機緣,捨離種種的方便法門。到了天台智者、永明延壽、天如維則、梵琦楚石等諸位大師,既悟般若無生之旨意,又開念佛往生之法門,難道這不正就是所謂圓融性相、兼攝三乘的大通家嗎!
而所謂的『出家』,不只是指辭親割愛而已,實在是想要出三界之家。能夠往生極樂,才是真正的出家。像前面智者、永明等這樣的大德,或者由禪宗而入淨土,或者即阿彌陀佛而明白我們的本心。掉身在娑婆世界的污泥之中,而能解脫生死輪迴之痛苦,此也是極盡大丈夫所能之事啊!
往生比丘尼第四
劉宋
慧木
慧木,俗姓傅,年十一歲出家,居住在梁郡(安徽合肥縣東北),建築村寺。每日誦大品的《般若經》,常有種種的靈異感應。曾經夢見自己到了西方極樂世界,見到一座浴池,其中有蓮華,有很多化生的人,安坐在蓮華之中。
不久之後請師父為她受戒,在戒壇之中,忽然見到天地之間充滿光明,皆是黃金色。有一天,和大眾一同禮拜無量壽佛,拜倒在地上而不起來。有人用腳踢她、問她何故?她說:「當我拜倒在地之時,突然覺得自己身體已經到了極樂世界,阿彌陀佛為我說小品的《般若經》,已經說了四卷,因為被踢而覺醒過來,現在實在是很悔恨未能聽完經典!」劉宋文帝元嘉十四年(西元四三七年),當時慧木已經六十九歲,後來不清楚她的去處。(法苑珠林)
劉宋 法盛
法盛。俗姓聶,清河(江蘇淮陰縣)人。劉宋文帝元嘉十四年(西元四三七年)時,年紀已經七十多歲了,出家於金陵(南京)的建福寺。法盛才識過人聰敏穎悟。曾經告訴一同修行的曇敬、曇愛說:「我立身行道,志在求生西方淨土。」元嘉十六年(西元四三九年)九月二十七日,在佛塔下禮佛,到了晚上突然身體不適,病情每日加重。就在當月月底的傍晚,正在小睡的時候,突然見到阿彌陀如來,從空而下,與觀世音、大勢至二大士談論二乘法,光明顯著照耀四方,寺裡的大眾皆感到驚異。法盛把她所見的境界全部告訴大眾,說完之後隨即往生,時年七十二歲。(比丘尼傳)
唐 淨真
淨真。唐代人,居住於長安城的積善寺,每日搭袈裟乞食。曾經誦《金剛經》十萬遍,平日專志念佛求生淨土。有一天,告訴弟子說:「我五個月來,十次見到阿彌陀佛,兩度見到寶蓮華上有童子遊戲,我已經得到上品往生了!」說完之後,立即結跏趺坐而往生,當時祥瑞的光明照滿寺內。(佛祖統紀)
唐 法藏
法藏。唐代人,住在金陵。平日精勤專志地一心念佛。有一夜,見到佛菩薩的光明照耀寺內,然後就安然往生。(佛祖統紀)
宋 悟性
悟性。宋代人,居住於廬山,平日專志念佛,求生西方。有一天,忽然聽到空中有音樂聲,接著就告訴左右的人說:「我已經得到中品往生了,而且見到諸位一同志向念佛精進的人,在極樂世界都有蓮華等待他往生。」說完之後即刻往生。(佛祖統紀)
宋 能奉
能奉。浙江錢塘人,專修淨土法門,常常見到佛光照耀她的身體。有一天,毫無疾病,告訴她的徒弟說:「我往生的時候到了!」不久之後,大眾聽到她念佛的聲音極為高亢懇切,於是前往探視,仔細一看,能奉已經合掌面向西方而坐化往生。此時有異香充滿室內,又有音樂聲隱隱約約地向西方而去。(佛祖統紀)
宋 慧安
慧安。浙江明州人,住在小溪的楊氏庵。平日專修念佛法門求生西方,並持誦《金剛經》,無論寒暑都未中斷。常常在室內,見到佛光照耀下來。有一天,示現疾病,自己正身端坐,警戒眾人不可諠譁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,說:「佛來了!」命令大眾唱念佛名,然後迅速地坐脫往生,時年九十六歲。(佛祖統紀)
明 袾錦
袾錦。字太素,俗姓湯,杭州人。出家前嫁於同縣的沈姓儒生,即是蓮池大師也。蓮池大師出家時,袾錦年僅十九歲,有人勸袾錦阻止蓮池大師出家。袾錦說:「常常聽到他說生死事大,阻止他出家,是誤了他,不可以的!」袾錦到了四十七歲時也出家,受具足戒。奉持律儀極為嚴謹,虔誠專修念佛法門。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(西元一六一四年),得疾病。病重垂危的時候,忽然告訴侍者說:「經典說十念就可以往生,趕快扶我起來!」起床之後,則端身正坐念佛而往生,時年六十七歲。(孝義庵錄)
明 廣學
廣學。俗姓龔,蘇州(江蘇)崇明人。年十二歲時,即斷肉食,平日受持經,朝晚虔誠恭敬地禮佛,自己發願不嫁人。年二十八歲時,剃度。前往杭州,依止孝義庵的太素(袾錦)法師而居住。專精奉持清淨梵行,純一而不雜亂。廣學體質一向虛弱,可是窮盡心力專事苦行,勤勞苦修而不吝惜自己的身體。不久之後得疾病,捨棄醫藥,一心等待命盡往生,因此氣息奄奄體力不振。
有一日,忽然自己起身,面向西方,端身正坐。庵主為她設立阿彌陀佛的聖像,廣學雙目凝視仔細地觀看,雙手合掌至心歸命。不久之後,盥洗雙手,穿著清淨的衣服,手持念珠,端身面對佛像,如入禪定。侍者恐怕她會傾斜跌倒,以兩個枕頭支撐著她的腋下,廣學揮手說:「不用這個!」大眾環繞著為她念佛,她又揮手說:「我自己有主,不必勞動大眾!」說完後就跏趺不動。經過兩個晝夜之後,以低微的聲音稱念佛名,氣息漸漸急促,然後寂然地往生,當時為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(西元一六一一年)二月七日,時年三十三歲。(孝義庵錄)
明 成靜
成靜。字實修,廣州東岡人。從幼年時,即奉持齋戒。後來出家,受具足戒。平日修習念佛法門不曾停止。曾經勸勉大眾造栴檀木的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聖像。到了明年,得了些微的疾病,預知往生的時至。告訴弟子說:「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,來此接引我,我去了!」說完即閉目而往生。(觀音慈林集)
清 潮音
潮音。俗姓金,蘇州(江蘇)常熟人,嫁給龔姓人士,後來守寡獨居嚴守婦節,與兒子端吾,一同發心出家。端吾既已出家為僧,潮音也到蘇州,禮拜比丘尼真如為師。後來回到故里,租屋而在其中修行,日夜六時,念佛的聲音浩浩不斷。有一天,示現微疾,自己沐浴後披衣,端身正坐在中堂,日落黃昏時,自己計算說:「亥時(晚上九~十一點)就要去了!」。後來把手收入袖子裡,端身正坐而往生,年七十三歲,此事發生於清世祖順治年間(西元一六四四~一六六一年)。(潮音事略)
論曰:「我收集古代比丘尼修習淨土法門而有傳聞的,不過是寥寥的數位而已。我想恐怕是流傳下來的都散失了呢?或者是女眾多隨世俗浮沈,自己能自我克制振奮精進的卻很少呢?然而留下來可以傳誦的大多都能謹慎地持戒誦經,堅定往生的誓願,臨命終時現諸瑞相。現在取錄而流傳之,以為修行的正確軌範。」